 咨询热线: 020-87377802 020-87374117
咨询热线: 020-87377802 020-87374117
叙事治疗的世界观
分享人:文洁
• 中山大学本科毕业,留学美国波士顿BostonCollege攻读咨询心理学硕士学位。跟美国叙事治疗大师JillFreedman和GeneCombs学习两年的叙事治疗,完成基础培训(学时120小时)。完成广州社协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主办的家庭辅导研修班——叙事治疗培训。完成游戏治疗师认证连续培训课程(北美)第一期。在美期间,于当地小学担任实习心理师一年。在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担任团体心理辅导师,以团体辅导方式帮助本科、硕士留学生处理跨文化适应问题。
• 运用叙事治疗辅导被强迫、焦虑、抑郁等状况困扰的成人,辅导希望改善情感与亲密关系、亲子与家庭关系的个人和家庭,陪伴来访者抽离备受问题困扰的状态,重获生命的丰富色彩。
• 带领受行为及情绪问题困扰的学龄儿童叙事治疗小组,令儿童的行为及情绪出现明显的改善。
• 为广州猎德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工,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培训“叙事治疗入门课程”。
分享内容:
1.研究叙事治疗的原因?
2.叙事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?
3.叙事的(后现代的)观点怎么看待人?
4.叙事治疗的技术
为什么迷上叙事治疗?
我记得当时是在美国上家庭治疗的课,读课本读到叙事治疗的那一章的时候,我眼睛都发亮了:里面讲到世界上没有标准的答案,每个人都是面对自己问题的专家,这些是我非常认同的观点。后来教家庭治疗的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节叙事治疗的介绍课,我就更加着迷了。每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的问题,并不只是被动地被问题践踩。
我今天希望可以讲到叙事的世界观,叙事如何看待人,如何看待现实,希望可以讲到部分的叙事的技术,有时间的话希望可以讲到案例。
叙事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?
下面我会讲两个故事,我想邀请你们推测一下故事里的主人公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?
第一个故事
某君,他出生的时候,母亲才18岁,他还没满1岁,他的父亲就抛弃妻子。后来母亲改嫁生了一个妹妹,他6岁的时候就被母亲和继父带到一个穷乡僻壤,在那里读小学的时候被同学戏弄欺凌、人身攻击。再后来母亲又与继父离婚,可是母亲选择留在乡镇里,他被送到跟外公外婆一起住。中学时代的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,整天在街头游荡,逃学,是每一个老师的噩梦,甚至还染上了吸毒和滥交的习惯。
第二个故事
某君,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混合家庭,有母亲和继父,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,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家还是挺不错的。小学时代的他有朋友跟他一起踢球、爬树摘果子。家里经济条件不错,所以从小学到高中读的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。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活跃分子,英俊潇洒,很多女孩子青睐他。高中毕业后,考上了一个不显眼的大学读本科,可是后来转学到全国最好的重点大学修读一个不错的专业。
第一个主人公面对很多人生的挫折,第二个主人公看起来经历比较顺遂。其实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同一个人,是两种对人生经历的解读。不同方面的解读会有很大的不一样,不同的故事塑造了不同的现实。我们说出来的故事也会塑造我们的人生。其实这两个都是奥巴马的故事,版本的真伪我不敢判断,因为政治人物的自传很可能也是他们想展现给公众的版本。(也就是现实是被故事所塑造的。)
下面就开始进入到叙事工作者最重要的理念,叙事的世界观,在这个部分我会说得详细些,因为叙事的世界观是叙事治疗最重要的指引,是基础中的基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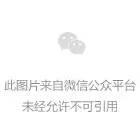
人的一生中发生许许多多不同的事件。每一个事件可以被看做这幅图里面的一个点。
通常当我们在咨询室见到当事人的时候,通常是因为他/她自己认为(或她被别人认为)人生的故事线是一个问题故事。正如图里面连起来的那根蓝色的线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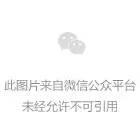
回到刚才第一个故事:例如:被亲生父亲抛弃、跨文化移居到穷乡僻壤、被同学戏弄欺凌、人身攻击、母亲又与继父离婚、被送到跟外公外婆一起住、整天在街头游荡,逃学,吸毒和滥交,假如将这些点连成一条线,那么这条线的名字可能叫悲惨的人生,现实工作中,我们会询问当事人给问题取个什么名字,所以其实也可能叫别的名字,关键是要贴近当事人的经验。
好,也可能会听到另外一个故事,出现第二条线,例如:他的外表是黑人,黑人在美国做了街头抢劫的事,很多的黑人贩毒,很多的无家可归者都是黑人,他吹嘘自己的父亲是非洲王子,这些点连起来就是另外一条线,名字可能是叫对黑人身份的鄙夷。图上显示就是橙色的线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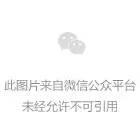
当这样一个有着悲惨人生,又鄙夷自己黑人身份的人出现在你的咨询室,你会怎么看待他呢?很多时候很容易会陷入困境,感觉到当事人的无望。如果是一个叙事治疗师,会记住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关于这个人的单薄的问题故事,而这个人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被呈现出来。叙事治疗师的任务就是找出不同于问题故事线的偏好故事线(Preferred story line)或者支线故事(the alternative story)。
那怎么找偏好故事线呢?
其实有好多种方法,我现在先讲第一种方法:寻找独特事件(unique outcome)。独特事件就是不会被问题故事线预测到的事件。像是下面这幅图里红圈里面的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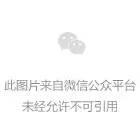
在刚才的奥巴马例子里,后来他读大学时转学到全国最好的重点大学修读一个不错的专业。这个是一个不会被问题故事线预测到的事件。
又例如,一个15岁的少年,经常在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就大发脾气,砸坏东西,打伤旁人,某一次也出现了事情不如意的情景,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又大发脾气,砸坏东西,打伤旁人对不对?可是他没有这样做,相反他冷静地走出了那个不如意的情景,去了学校的体育馆。那这个“冷静地走开”,就是一个独特事件,因为他“遇到不如意就大肆破坏的问题故事线”不会预测到这个“冷静地走开”。
好,发现了一个独特事件以后,叙事治疗师会希望发展一下这个故事,一步步通过问出发展故事的问题,从最熟悉的经验由近及远地问到这个故事显现出来的人们的意图,渴望,梦想,他们拥护的价值。假如问出这个15岁的少年在这个事件上反映出来的渴望是“有权利掌控自己的生活”或者“有权利去享有私人空间”(这条故事线也是由当事人命名)……叙事治疗师希望往前找到反映着相似主题的事件。
正如这样,往前开始连上点。找到几个以后,就可以连成一条较偏好的故事线,故事线的名字是“有权利掌控自己的生活”。就是那条紫色的线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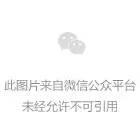
问题故事线也许不止一条,较偏好的故事线也不止一条,人的生命就有了好多好多条线。值得注意的是,问题故事线并没有消失,我们并不是抹掉了它,只是因为画了很多条线,原来一开始或许很粗很显眼的问题故事线显得不那么明显。相较于原来的单一问题故事线,人的生命就呈现得出更多元化的状态,而且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变成这样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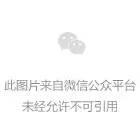
这个观点是很好用的。再举个例子,假如你遇到一个入院多次,试图自杀多次,觉得生命已经绝望的人,如果用这个叙事的世界观来看,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?
大家回应得都很好,比如询问:什么让他熬到现在?除了绝望,生命中还有没有其他不绝望的事件?寻找例外事件的好方法就是问问题:“有没有一个时刻你原本是可能被问题控制住的,可是问题并没有得逞的呢? ”寻找入口还有几种好方法,以后有机会可以分享。
“入院多次,试图自杀多次,觉得生命已经绝望了”,是因为这个人的问题故事线非常非常粗,粗到他/她已经没办法看到别的故事线了。可是作为叙事治疗师,我们会提醒自己这个人一定有其他的故事线,我们可以帮助他/她找回来她。刚刚大家的回答里有些就是在找其他的故事线。
我们通常看到的第一条线就是问题故事线,原来这条线很可能就是当事人人生的主线。我们希望发展他偏好的故事线,让他可以用偏好的故事线作为自己人生的主线。而且我们会咨询询问来访者的偏好,例如他的梦想,意图,渴望,承诺,价值等等,发展他自己选择发展的故事线。如果不确定哪个相关,会询问当事人,由当事人决定。
小结一下:
叙事治疗认为,当事人来到咨询室的时候,通常是因为他/她自己认为(或她被别人认为)人生的故事线是一个(或多个)问题故事。但其实人的一生中发生许许多多不同的事件,有些与问题故事相符,但也总有些与问题故事不相符。如果是一个叙事治疗师,会记住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关于这个人的单薄的问题故事,而这个人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被呈现出来。叙事治疗师的任务就是找出不同于问题故事线的偏好故事线(Preferred story line)或者支线故事(the alternative story);令单薄的人生故事线变得丰厚——意思就是人可以重新将多重故事线编写到人生故事中,人的生命就呈现得出更多元化的状态,而且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叙事的(后现代的)观点怎么看待人?
结构主义也就是现代主义,主张把人分类,贴上标签,按照类别来处理。人的性质是固定的,是固着的。所以关注的问题是“你是谁”。不论是好的特质,还是坏的特质都被内化到个人,例如我很焦虑的人,我是好奇的,或者有创造力的人。另一个例子是人被分类成有抑郁症和没有抑郁症。在治疗中,经常会容易将人的身份会被全然化到只有问题。人好像一个个被分类好的香料瓶子,被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面。
后结构主义呢……给大家看一幅图:
嗯,如果我问你这朵花是什么颜色,你会怎么回答?
它不是恒定的紫色,或黄色,一直在变,所以很难归类它是什么颜色对不对?无法归类,因为它一直在变化。后结构主义用流变的方式来看待人,正如那朵花,一直在变化,无法被归类。人的身份是意图的,是未来取向的,是发展的,是不断变化的,是在过程中的。
关注点在:人可以怎么成为他/她想要成为的那个人?
人是可以变化的,这一秒是这样,下一秒可能就不同了,取决于人选择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。可能我选的这朵花的变化不够多,它变化是有规律的,人的变化也许也有规律,但也或许没有规律,后结构主义相信人的生命可以有很多不同方向的变化,也是具有很多的可能性的。
这一点和刚才那个点点的图整合到一起来思考的话,会得出:人是有多元化的多条故事线的,哪个时候选择哪一条故事线作为主线,也许就呈现哪一个状态,所以人的身份是可以从认同问题故事线,变成认同偏好故事线的。举例来说,抑郁是问题故事线,可是人除了抑郁还有多条故事线,还可以有很多变化,人可以选择认同他/她偏好的故事线。
问题有时候很令人生厌的,可是有时候也是对人有益处的。也就是说问题也不是全然化(Totalize)地只是问题。叙事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:问题是问题,人不等于问题。既然问题不在人的里面,那究竟在哪里呢?
我们把问题定位在主流价值论述之中(locating problems in discourses)。意思是因为有主流论述的存在,所以问题才会存在。主流论述,也可以说成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评断。举例来说,因为有“男主外女主内”这样的主流论述(又甚至是描述伴侣只用男女的主流论述),令事业心很强,或者不做家务的女性被看做是有问题的,还有家庭主男也被看做是有问题的。再举例来说,同性恋的关系,在中国的主流社会评判中还是比较困难的,可是在别的国家,就是换了另外一种主流论述,早就不是问题了。问题会存在,是因为主流论述的存在。可是如果换了主流论述,问题就可能不是问题了。
我说这么多世界观,是因为我的老师JillFreedman经常说一句话,叙事治疗的工作里面世界观是最重要的。只要用的是叙事的世界观,用什么技术是不太要紧的,不同的叙事治疗师都有不同的做法。可是假如没有用到叙事的世界观,就算使用了叙事的技术,也并不是叙事治疗。而且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论的世界观。
在实际的会面工作中,我们会用这样的世界观看待当事人,但是并不要求他接受,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些,可是他的状况也是能变好的。我们把故事的写作权,建构权都交给当事人,我们只是在引领他/她走这个过程。基本的架构也是遵循既要看到问题故事,也要看到偏好故事。并邀请当事人丰厚地描述问题故事和偏好故事。以后再重写故事的时候也遵从当事人的意愿。
叙事治疗的技术
叙事治疗的几个假设:
1.问题才是问题,人不是问题,人与问题是分开的。 所以我们会用到“外化”的技术并把问题赋予形象,赋予个性,把问题从人身上分离出去;
2.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“专家”,是自己问题的专家,没有人比她/他更了解自己。当事人对自己的生活拥有专家知识,治疗师则是将这些专家知识带出来处理的人。叙事治疗师在治疗中的定位:a.治疗师的去中心化(de-centering)和有影响力(influential);b.不假设自己知道(not knowing),不要带着自己的假设去听当事人的故事;c.不以“专家”姿态自居(White,1991),不试图给建议或分析他人;d.不评判,不论断。
3.每个人本身才是自己生命的作者,每个人都有能力依照自己的偏好,重写自己的生命故事。所以我们有重写(re-authoring)这个技术。
4.人总是在应对问题的,问题不会百分之百的操纵人,人的一生中,总有几次不被问题影响的例外经验。 (也就是刚才讲的点点图的那一点)
具体的治疗技术有:
解构(deconstruction)—外化(externalization)
重写(re-authoring)
重记会员 (re-membering)
仪式 (definitional ceremony)
治疗档案 (documents)
局外见证人小组(Outsider Witness Group)
小组叙事工作
社区叙事工作
叙事的技术是一块一块的,并没有标准流程。可能第一次会面就用上remembering,或者解构。重要的是跟随来访者,见招拆招
叙事治疗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问题——
› 拖延、压力、情绪、亲密关系、转变适应、人际交往;
叙事又特别适用于
› 厌食和暴食等饮食心理障碍
› 中重度负面经历(急性危机创伤和慢性创伤)
› 哀伤辅导(丧亲、失独、失业、失恋)
› 跨文化转变适应(升学、移居、人生新阶段)
› 跨身份认同(性别和性向认同)
› 服务儿童青少年、长者群体
总而言之,叙事适用于服务与主流文化不同,被边缘化,被区别对待,被灾难和暴力侵袭的个人、群体和社区。 另外,叙事的督导过程非常有趣,非常类似于叙事的治疗过程,督导用的技术跟治疗用的技术基本是一样的。
一般来说,具有基本的语言和思考能力的个人就可以做,例如4岁的小孩子也可以做,具有基本的语言和思考能力的自闭症个人也可以做。 所以叙事对普通人想要探索和成长也很有用,我自己就多次被叙事治愈。治愈以后感觉很轻松,很有力量,很有希望。
我想今天差不多了,用创始人之一的麦克·怀特的话来做个结束语:
把这个学说定义成一种世界观是不是比较好呢?也许吧。可是即便如此,也还是不够。也许应该把它说成是一种认识论,一种哲学,一种个人的承诺,一种策略,一种伦理,一种生活方式等等。
——麦克·怀特(Michael White),1995
-叙事治疗书单-
推荐初学者可以读:
《叙事疗法实践地图》(台湾版:《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》、英文版<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>)
我读的是英文原版,他写得非常有趣生动,解释简洁明瞭,好像台湾版翻译得不错,大陆版我没有看过。
想深入了解者可以读:
《学校里的叙事治疗》 (<Narrative Counseling in Schools> )
《说故事的魔力:儿童与叙事治疗》(<Narrative 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> )
《儿童叙事治疗》(<Playful approaches to serious problems> ,有台版和大陆版)
《解构并重写生命的故事》(<Narrative therapy: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ies> )
<Narratives of Therapist’ Lives>( 只有英文原版)
<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> (有台版)
一般来说,台湾译者翻译得比大陆译者的要好理解很多。其实更加推荐的是上Jill Freedman的培训班,边听课边练习,亲身经历叙事的做法理解最深,获益最多,因为是真正浸泡在叙事的世界观里。